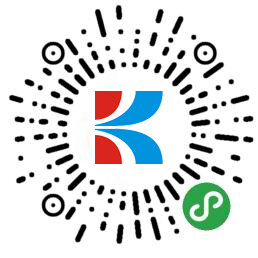五点从公司出来,便往罗湖火车站赶,凑巧碰上开赴香港的军车队,只得慢慢等候,幸好在七点正赶到罗湖。胡乱买些香烟水果与书刊,便随人流上了开往常德的N594次。仅凭脸型,便断定邻居铺位全是常德人,本人一向自感与常德MM没有发生任何故事的可能,早早便睡,竟到长沙才醒,好不幸福。
八点半,出得益阳站便上了回家的巴士,这个时候,家的意味,突然真切而强烈了起来。事实上,我是个很恋家的可怜家伙,尽管这些年一直过着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非人生活,却一直迫切地想真正的全方位的充当一个称职的儿子、丈夫和爸爸的角色。掏出手机,告诉爸妈自己的方位和到达的大概时间。
巴士向南蜿蜒于山间,工业的气息越来越淡,越靠近大山,满眼的绿越来越柔润。远处是黑青的大山轮廓和蓝的无法描述的天空,路边的洢水泛着清亮的波光北向蛇行远去,两岸是微风中或向阳翠绿或背阳墨绿的毛竹的海洋。家乡的风景,是天然而别致的。
果不其然,远远的便看到了前方两熟悉的身影候在路边,见儿子的心情,同见爸爸妈妈的心情,一样的迫切。下得车来,上下仔细扫描了他们两个,还是过年时的那样子,甚至稍显年轻,心情便高了起来,丢掉挎包,抓起老娘的手,看到只是有些儿不太灵活,心情整个就飞了起来。老娘,又背转身擦起了泪水。
又一次,到家了。
刚落座,奶妈也闻讯从镇里赶了过来。生为人子,我是幸福的,只是我这个儿子,做的远远不够。
才开叫的小公鸡的味道,就是鲜,老头泡制的酒,就是香。
午餐毕,列出明日所需的大件清单,打电话给超市于某时送来,给三老家伙递上自己的孝敬。便开始了天昏地暗的拖拉机大战。
第二天,姐姐一家早早来了,小昊一下子就窜长到了将近一米六,老爸的外甥陆续驱车前来,生日宴热烈而丰富,老爸嘴角眉尖一直处于飞扬的状态。送走客人,又是天昏地暗的拖拉机大战。
手气特好特红,基本每把牌都有两张王牌,甚至打8的时候抓了八个8。深感纳闷:老家伙忘了给我出考题了么?还是这次的考题就是没有考题?
三老家伙好似并没留意到我揣揣不安的表情,撑到12点便熬不住弃械投降,小石将下一步的计划合盘摊开:一、明年过年的时候,能够买辆经济适用的小车;二、争取碰上一个不管儿子是贫是富都愿意与我同甘共苦的女人。三老奸巨滑的家伙很高兴,开酒,继续拖拉机大战。
时间过的很快,前天就已买好去往长安的大巴车票。每次出来,爸妈都坚持在车站送我。
爸妈的身影逐渐细小模糊,熟悉而亲切的家乡景致快速地被大巴抛在后面。我,能够如期地实现计划么,能够全方位地充当好自己的角色么?或者,我能做的,就是努力的去做,真正地把握真实的当下,扎实稳步地向前推移。因为我晓得,偶尔的犯错机会和可以虚耗的年轻光阴,都是如此的奢侈。